川南在线 发布时间:2025-03-17
——读杜春翔诗集《迷宫与十二幻像》之感
□ 郭为民
常言水到渠成,用在诗歌创作上,这是一种技巧和态度。
黔北诗人杜春翔诗集《迷宫与十二幻像》,以你熟悉的历史传说典故为题,不是为了再次解读,而是“水到渠成”式的滔滔倾诉“天源之水”的祈福祈愿,绝不会按固定渠道走向,而是辐射式指向一切生灵之壤,与千草万花共赴一场灵魂舞蹈盛宴。
此诗集结构上有十二个部分:弥诺陶洛斯,迷宫与十二幻像/纪念德彪西·海浪的和声/荆轲刺秦/古濮人的河/风零饮:东行漫记/小苍茫/群山之心/牂牁纪事/岳武穆散记/β牧场,AI与人/逐鹿之书/嶙峋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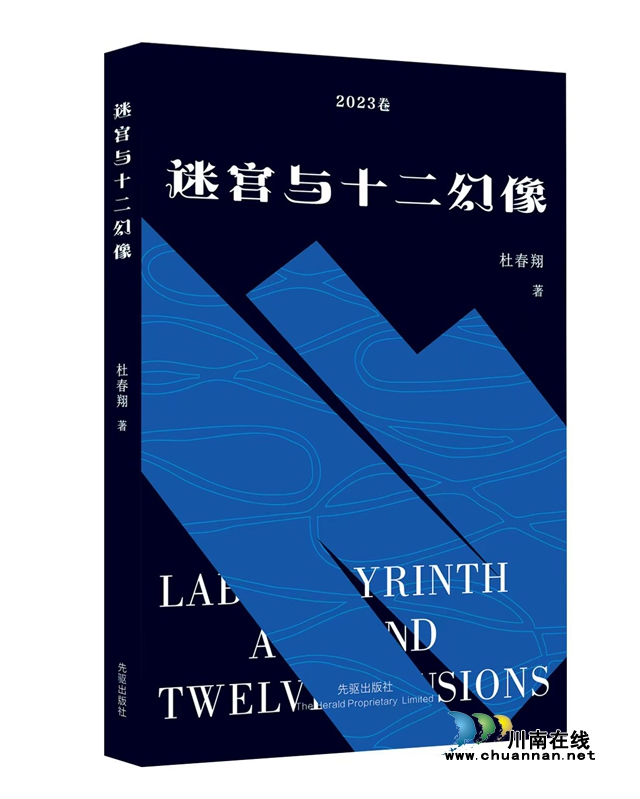
从欧美古老神话到中国华夏传说,再到黔北大山深处的民间故事及古老山民生存环境的一草一木、一池一地,都成为他摘取诗歌表达意象的水源,古朴并带有几分原生态的真情恣意奔放流露,时时感觉到呈现一种内容与形式“供不应求”的承接关系,是“内容”饱满到“胆大忘为”的地步,满世界寻找最恰当又最出乎意料的形式载体,就像一股股泉水散伏而出,流到哪哪就是心灵的家园,那里有阳光也有寒月深处的忧伤。
“……那时,风吹过山谷/小豪猪竖起全身的坚刺/浆果,红色的浆果/豪猪和兔子们喜爱的浆果……”(《弥诺陶洛斯,迷宫与十二幻像》之《森林里的浆果》)。
谁能笔触间闪出“小豪猪”“兔子们”?憨憨、小小的、乖乖的,为了“红色的浆果”,竟要与牛头怪对峙一番:“……但牛头怪,要把石头变成野兽/把野兽变成白骨/让弱小的,不合群的,无助的群体/在虚无的时间中旅行。”
但“浆果”实在诱人,那弱小的豪猪与兔子们,没有理由放弃获得。这个答案在《破冰》里找到了:
“……这慢于光速的宇宙深处/相对论统治的短暂里,世界被集体禁言/破冰的巨手破空而来/星河不再绚烂,灵与肉,人与兽/大地的女儿,将展开悲壮的史诗。”
实际上,诗意是要打破什么的,一旦打破,绚烂的光会闪出诡异的思想与想像,因为“天源之水”会带来什么,发生之前都是未知。
“安提比小路旁的火红玫瑰/戛纳的浓云与烈风,在通往大海的幽径上/不息着,挪威木工的歌声/我和大海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我是其中的一滴水……”(《纪念德彪西·海浪的和声》之《少年的清晨》)。
在这一部分,诗人不是刻意去解读德彪西的独创音乐,而是在遥远的乐曲中寻找他需要的灵魂的东西。与其说是德彪西的音乐点穴了他某个敏感部位,不如说是诗人沉积于血脉的基因,在宇宙的某个座标与西方音乐的“艳遇”而产生共鸣,是诗人把这种“天源之水”引到我们眼前。
“我曾经听从本能的指引/将阴藏在缺陷里的细节,狂怒的真理/痛苦的片段一一敲击/像那些大河之上的荡族群/用马匹横扫了富庶平原……”(《纪念德彪西·海浪的和声》之《反教条》)。
音乐如水,谁说天源之水不是音乐?也许是德兄音乐的某个高音击中了东方古老神秘土地的某个伤痛,诗人要表达出来,“……但我不会从事劫掠,挖祖坟,焚毁庙宇和宫殿/我也不信他们的神/我要朗照的天空,柔和明亮/有精致云朵。”(《反教条》)。
然音乐和天源之水终是心怀柔和与美好的。诗人正是以”我要朗照的天空,柔和,明亮”的潜意识,让诗意在一种和谐的节奏中最恰当而又出人意料地“捕获”惊艳的词句,从而与“上帝”胜利汇合。
这种水到渠成的天意汇合,在该诗集各个部分都一再出现,极为自然。
“我爱那峰顶的危崖,孤松,流水/惊涛低吟的回忆,莫奈弄月的光影/像风浪中挣扎的水手/十指试图,从内心取走另一种声音/取走,一些透明灵魂。”(《浪子》)。
谁说“水往低处流”?在《迷宫与十二幻像》诗集里,诗人心中处处流淌天籁之音天源之水,即便是“峰顶的危崖,孤松”也能受此惠泽而富有生命的尊严。
第三至第十二部分,这种水到渠成的天意汇合与最恰当而又出人意料地“捕获”惊艳的词句,呈现更多。
“在虚时间中漫游,剑客的青春/曾输给一位剃头高手/此后拜伏过耕夫,诗人,水手/那时,剑从未出鞘/摘飞花逐落叶,拟正电子加速的航线/从赵国的废墟到燕国的邹衍庙/像从一个彼岸到另一个彼岸/被时间以极轻的抚摸……”(《荆柯刺秦》之《少年的清晨》)。
在此,“刺”是微不足道的,诗人牵肠挂肚的是“剑客的青春”和“剑从未出鞘”,“荆柯”“秦”“赵国”“燕国”等等世人耳熟能详的历史词句,不过是诗人“天源之水”诗意表达的意象载体。
“今夜会有雪来/与炫目的寒光没有什么区别/你双手紧握冰凉剑柄/清辉出鞘/你终究舍不得人世间的美好/舍不得春风般发甜的记忆/剑出,这是上师残留的经卷/剑舞,缠绵刻骨之爱的苦痛……”(《荆轲刺秦》之《空旷之刃》)。
“……我坚持在无数相同的晨昏,目光/进入同一幽谷,看七十二峰外/剑客信步时,像赶羊的二楞子/夕阳尽处,不知去向”(《云雾叠翠》)。

诗人在“剑客”身上找到一种意境,或是暗指或想起自己某次历险时的光景,有一丝孤苦又有一丝无人所知的甜蜜。
“我们因深处孤独而如此怀旧/仰望星空,希望找到更远的自己/五月的南方,开花的树枝,摇摆的草裙/夹缝岩下窜出匹野马/后面跟着一群持竹弓的濮人/他们以竹为姓,伐竹造屋,鼓喉作语/太阳的舰队曾停驻于此/或隐身五彩斑斓的天空/时间之上的古老风物/传奇与湮灭,像穿中起伏的刻痕……”(《古濮人的河》之《长江域·古帕依村》)。
从传奇剑客到老家的”古濮人”,在这本诗集的天源之水式的诗意表达中,身份可以互换,金属之剑并不比竹弓更且有追求欲望。前者是生而向亡,后者是死中求生,后者在诗意的世界似乎更有存在意义。“死中求生”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在诗人笔下的古濮人看来,一切宏大的哲学命题都不及“那个有点小雀斑的女孩”和“调皮的白狐”——
“……濮族在黑暗中曾举起火把/让万物的叹息来源于那种光/爱和生长的样子/从巨斧的边缘漫延/似水火般碰撞/少年戌,将从丹霞石后探出头来/他爱上部落里那个有点小雀斑的女孩/也曾用淬了麻药的箭簇射中过调皮的白狐/成长中历经倾泻阳光的颤抖、哀鸣和悲悯……/那时,物质的造梦师忘却了“活着”的真义/囿于外物的光鲜,迷失于扩张式语境”(《赤水域·丹霞山》)。
至此,诗人把这种水到渠成的天意汇合,落位在“古濮人的河”与“赤水河”左岸右岸,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绝不比西方神话、德彪西们缺乏神意与伟大。诗人在迫不及待地、天源之水似的讲述老家或曰“心灵家园”的那些具有诗意的诸多神奇的细节——
“……银河年十三虚岁,冬季后,阴影消融/阅尽荒芜者,空空如也的内心/向往崇高意义的拔节而升……如在郑板桥和毕加索艺术里/竹存在过,抒写短暂伤痕……”(《赤水域·竹海》)。
“……手执星盘的,结合流水的走势勘舆方向/让巨石成为骨骼深处最初的信仰/让山脉亘古的倒影,延续姓氏的墓碑生长……在水流般疯狂、激情的滩头/谁自认是鲸鱼的子嗣?/那些已远离大海,搁浅星空的人/逆行顺流,均已无关善恶”(赤水河·丙安滩》)。
“山脉与山脉间的契约/在流水的事实中彼此吸引、包容/但在∑Pi求和法则中/左岸与右岸曾对立/植物语言与动物语言之间/虚幻与现实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当数学和语言的符号退守/流水的音节便只剩下一种/在千万沟壑中,往低处走/于石骨棱峭穿云裂萼处成银河……”(《赤水河·左岸石岸》)。
“……镜泊湖之远,有一座尸山,毗临宁古塔/被披甲人持戈观望/……亮闪闪的元首楼,这像极了/欧佩克大厦,致力于消灭个体差异/对权威拥戴、孤立,暗藏杀机……白桦林可能是绥芬河最早的列兵/它们羞于繁衍,扩张/因白雪一样的皮色,可任抒情/含36种可能的恋爱式,两种理解道路……”(《风零饮:东行漫记》)。
阅读于此的这些诗行词句,难道不是来自一种与神的对话吗?这本诗集的几乎每一首诗,都打破了大多数人惯常的语言构架,呈现陌生感。一般而言,在一首或一组诗中做到于此并不难,但在一本224P上百诗都呈现同一语感,则不易。笔者以为这种不易,来自诗人对东西方远古神话及生命的彻底关切,并溶于对未来的思索,巧妙地摘取华夏神奇十二幻像的意象为表达载体,从而展现出一幅“天源之水”的诗意世界。
如《小苍茫》之《阿那耶》:“……我是被石头诅咒的穴居者,习惯追逐河流迁徒/多次被迫逃离,在困顿中选择自救……”这无不使人想起渔猎时代的渔人,是诗人“捕获”的诗歌意象,亦是“渔人”闯进了诗人的“天源之水”。我认为这是最高的诗创技巧。
又如《群山之心》之《分层透视》:“常在群山中博浪练习/目光追随云朵,轮廓模糊处,重叠锻打/像汉语表达一次错误分行。我拒绝……”诗人此处的笔触,陡然放眼至冰川纪白垩纪时期的地质运动,记忆深处绝不忘却故地之群山曾是壮阔海洋,“群山之心”其实就是海洋之魂,诗人拒绝“甘于现状”者。
这种“拒绝”,奋勇向前探索的欲望,在《逐鹿之书》的《酒神帖》中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些颤动的芳香光环/像少女初开的歌舞/……请予我疯狂回应/予我神圣的心一起向前飞奔/我担负你的依偎/拥水与火的纯粹歌咏/在欢乐之园,请给我一只泥哨/让我有黑铁之劈/穿越黑暗,指向永恒。”诗行于此,笔者忽然感觉诗人是把天源之水与德彪西式的音乐同产自大山深处的酒“混”为了一坛,才“意外”获得神之助力。多么奇妙的“黑铁之劈”,又多么神奇的“酒神帖”。
我敢保证,如果诗人不是深居黔北那条神一样的、濮人爱过恨过的天源之河,就不会在诗歌的DAN里找到解开“十二幻象”的密钥。
这个“密钥”在诗集的结尾《嶙峋明月》得到印证:……山谷里的风吹荒草不留痕迹。/一一回到了茅台镇,像回到现实/霓虹夜幕,彩虹桥,茅台国际大酒店/赤水河的水清冽,下沙的时刻近了……”
难道“天源之水”就在黔北那条滴水成酒的河床深处?
【诗集作者简介】
杜春翔:笔名补一刀,安顺囤堡人,现居贵州遵义。作品散见于各文学期刊和多种诗歌选好本,著有诗集《轮回》《鼓动苍茫》《迷宫与十二幻像》,财经类著作《30分钟学创业》等。
【本文作者简介】
郭为民,贵阳人,现居遵义市播州区。曾任广西经贸时代报、北海旅游报、泸州晚报、泸州广电报记者、编辑、值班编委等职。1990年代起在《山花》《花溪》《星星诗刊》《散文诗选刊》《神剑文学》《贵州日报》《遵义文艺》等发表诗、文数百首(篇)。
(完)
编辑:李永鑫

关注川南在线网微信公众号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 ,获取更多最新资讯
文苑